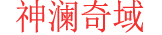
章六十一 轻别离
| 上一章:章六十 兴亡 | 下一章:章六十二 意决 |
天才一秒记住本网址,www.shenlanqiyu.org ,为防止/百/度/转/码/无法阅读,请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本网址访问本站,记住了吗?
尹清微微点头,“我本也没打算在朝中掀这一出浪。大人一日未到舒州,此事便一日不可告白于朝中。倘让皇上知晓,以其手段雷霆之势,必不能容大人存活于世。”
她眼中忽而透出些光,转而又逝,口中淡道:“是啊。”
外面天边露白,晨曦淡扫窗橼,有鸟儿轻鸣的声音偶尔传来。
孟廷辉起身,伸手捻熄了灯烛细苗,道:“时已不早,怕枢府会有人四处寻我,我先走一步。”
尹清注视着她,良久才又拾笔,重新摊开一张纸。
外面晨风极是冷洌,远天青白云雾一片混沌,半盏银月尚未褪去,依旧挂在殿角斜处。
她走着,浑身上下止不住地发冷。
足下好似是柔软云端,一步一空,人像是一不小心就会栽下去。
不是不惊,不是不疑,只是惊疑亦无用。
自幼便想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,却不想有朝一日竟会从天而降这一脉血海深仇来。
她不敢肯定自己真是这等身世,可是她肯定与否,都已不重要。
那些亡国之恨破家之仇,那一杆杆银枪一簇簇利箭,浑然拼就成一张遮天蔽日的大网,精准地朝她罩下来,令她避也避不开。
北地那数万前朝遗民所聚之由,不过就是她这一个前朝皇嗣的名号。
是与不是,根本不是她眼下能自己说了算的。
可这世间又哪有什么对错爱恨是真让人一语能了的。
她自幼孤苦,每每夜深人静时总渴望能像别的孩童一般依偎着父母,汲取那一点点温暖。
但她此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温暖,就是那一年的那一夜,那个少年宽阔有力的怀抱。
……若吾身可济民,吾不所惜也。
北境烽火流寇致使多少人妻离子散,又有多少个孩童如同她当年一样永失父母、再无可依可靠之人?为了报这一场亡国破家之仇,可真的值得赔上这万万百姓们的苦乐悲欢?
他的父王诛杀了她的父母她的宗亲,可她却因年少时那一个温暖的怀抱而从此万劫不复地爱上了他。
心甘情愿地伏在他脚下,不计所报地为他付出,无论做什么、无论怎么做,她都绝无怨悔。
哪怕将来有一日让她去死,她亦不会后悔。
这是多么的讽刺。
那一夜雪山温泉中他的话字字彻骨,在这初夏清风中于她耳侧翻荡不休。
……我若动情,天地可鉴,江山天下是为证。
恍惚间又想起夜里沈知礼才说过的话,皇上何其心冷,私情一向不足以乱国事。
只不知当此大乱之际,倘是他知道了她的身世,是要顾他的江山天下,还是要顾她?
她的心口麻麻的。
他是她的明主,更是这天下百姓们的明主,她不愿与这江山天下,去争这一个他。
从前的她为了他和他的天下,做什么都甘愿。
可这天下亦是百姓万民的天下,如今倘为百姓计,她又如何不能再心甘情愿地成全他一次?
……若她身可济民,她亦不所惜也。
金阳光芒自云缝中四射而出之时,她恰已走回睿思殿阶前。
外面候着的宫人看见她来,忙过来相迎问礼。
她问人:“皇上可是起身了?”
宫人低头答:“皇上一夜未寝,也没人敢去打扰。”
她点点头,也不着人通禀,便径自上阶去叩殿门,在外道:“臣孟廷辉求见陛下。”
里面久无应声,她便兀自推开殿门走了进去。
他在御案旁的矮榻上斜靠着,手中握着一本奏章,双眸却是微微闭起,眉间一片疲态。
她关门的声音有些大,一下便令他警醒过来。
他触目望见她在朝阳下的笑脸,眉间深褶才平展了些,低声道:“不经通传就私自入觐,谁给你的胆子?”
她朝他走过去,微微抿了唇,竟是直通通地在他身前跪了下来,垂首道:“陛下,臣欲出使北境以谘和事。”
他凝眸打量她,随后便是一声低喝:“你给朕出去!”
她纹丝不动,轻声道:“陛下倘不允臣,臣便跪着不起了。”
他蓦地撑身坐起来,周身全是怒意,冷冷道:“孟廷辉,你不要逼朕。”
“臣没有逼陛下。”她抬眼望他,眸底清亮无暇,“眼下若要平北地安宁,必得暂缓北事而剿灭流寇;为国为民计,朝中非派文臣出使北境不可。臣忝列二府,岂能寝其位而不治其事?古相、方将军所言皆是,朝中别无文臣能比臣更适合出使潮安北境。陛下不允此议,无非是怕臣于北境之上有个万一;可金峡关如今为我军所掌,臣倘至军前,狄将军势必会内外护臣周全,不过是与北戬朝使议和罢了,又能有什么事儿?陛下且放臣去北境二、三个月,待寇祸稍止,臣便立即回京来。”
他语如锋刃:“绝无可能。”
她跪得端端正正,道:“陛下,臣想一辈子留在陛下身边,必得有所功绩才行。倘是此去北境能成大事,则往后朝中必没人再敢说臣的不是,将来亦有资历能入政事堂,不必再使陛下为难。”
他僵紧的脸色在听见一辈子三字时轻微一变,可却抿唇不语。
她温柔地望着他,想了想,又道:“臣尝与陛下言,但愿将来不会再有孩童丧父失母、孤苦无依,陛下可还记得?北面战火波及无辜之数何其多也,百姓若苦,陛下心中亦不会好过。倘是臣此番出使北境事成,必能使战事早些平止,陛下又何必执着于臣一人安危而不放臣走?”
他眸光渐变,她知道他心重百姓,因而便没再吭声,静待他的反应。
过了许久,他才微一闭眼,低声道:“孟廷辉,我是不是对你还不够好?”
她鼻尖一酸,强忍道:“是臣不知好歹。”
他倾身,一把将她拽起来抱进怀中,薄薄的嘴唇抵上她的额头,“既是这么想去,我便允你。”
这个怀抱是一如既往的温暖,暖到她连骨头深处都在打颤。
她亦紧紧抱住他,微微哽咽:“谢陛下。”
他抱着她起身,往内殿里走去,一路碰翻了好些东西都不管,横臂放她入榻,扯下御帐翻身箍她入怀,力道之大令她几乎不能呼吸。
她只觉骨头都似要被他揉碎,可却依然顺着他这力道紧紧地贴偎在他身前,恨不能就这样将自己嵌进他身子里去。
他忽然在她耳侧沙哑道:“孟廷辉,你还欠我一事。”
她想起来,他应是指当初生辰那晚之约,便微微笑道:“陛下如今想好要从臣这儿讨什么了?”
他轻一点头,大掌牢牢按住她的背,像是怕她会退会逃,低低的声音径直侵入她内心深处:“给我生个孩子。”
她浑身一震,呼吸窒住。
好似过了天长地久,她才反应过来他说了什么,心头渐起又苦又涩的细潮,人被这苦涩潮水淹得体无完肤,终开口道:“好。待臣从北境回来,便还陛下此愿。”
他低头,轻轻啄吻她的嘴唇,哑声道:“你不可欺君。”
她眼角有泪滑出,然嘴角却扬起,含笑道:“臣便是有天大的胆子,也不敢欺骗陛下半字。”
昏昏沉沉地睡过去,又昏昏沉沉地醒过来。
外面已是大亮,轻薄纱帐挡不去顺缝肆泄的阳光,柔滑锦褥被映出淡淡的光晕,点滴绚烂。
身边没人。
她拥着薄被,心知他是去上朝未回,又毫不惊讶他没叫她起身上朝。
经过昨夜,今日早朝定是在议北境诸事,而她出使北境的事儿想必会被当廷除诏,至于旁的,她也无心去管了。
权当是称病一日罢,既然他如此疼她,她也就任性着心安理得地享他这圣恩一回。
又躺着小寐了一阵儿,浅浅梦到瓢泼大雨中她浑身湿淋淋地站在荒野上,一下子被冻得透骨,继而颤抖着转醒过来。
她撩开帐子下榻,跑去窗边伸手压上那被阳光晒得微烫的窗棱,许久才缓过一口气来。
他不在,宫人自然也不敢入内打扰她。
此处是他平日理政夜宿的地方,而他竟会如此放心地留她一人在这儿,全然不怕她会不会做出什么不当的事儿来。
她索性也就随了自己的性子,放肆地在这空无一人的政殿中独自悠逛。
御案上的奏章放得整齐,朱墨紫毫、镇纸瓷洗纹丝不乱。
她随手翻看了几本,眼见那上面的朱批字迹草然有力,心底便是轻叹,又转身去望一旁的黑漆木几。
最靠里面的格子中,竟有厚厚一摞奏章单独放着,一本一本排得井然。
她有些好奇,不知这是何等要物,便大胆抽出一本来看。
才一翻开,她就怔了下,随即又抽出几本,看后眼底变得有些湿。
这些竟都是她这些年来上奏的折子。
大多是他未批复发还的,还有一些是关于她的敕谕草诏,全都被保存得如此齐整。
从她甫入翰林院直到如今身在二府,从他还是皇太子直到如今位在九尊,她与他在朝堂上的点点滴滴,历历映目。
她静坐下来,一本本地翻阅过去,偶尔能看见有些折子后他落了朱批,却不知为何没发回到她手中,而那些朱批中又透着他难得一见的私情。
有喜有怒,有称赏有责斥,然而却终究都没让她知道。
她看着看着,就忍不住落下泪来,又怕沾湿奏章,便忙将那些折子按原样一一收好,然后抹了抹眼睛,走回内殿去。
内殿中物什整洁有序,他的衣袍衮冕都被人收放在一处,一眼看去全是冷清暗色,黑灰青褐,绫锦缎罗,雍容华贵却毫不张扬。
她伸手一一触摸,又将脸埋入这些衣物中,轻嗅那带了他身上独特气味的衣香。
另一边搁着他的御弓长剑,鎏金耀眼,冷光刺目,厚重的衣甲含威带戾地堆在一旁,箭箙皮革有些已经磨得褪了色,却仍被擦拭得锃锃发亮。
她握住那弓渊,脑中想起那一次在马背上他亲手教她骑射的场景,那一句“我的女人”至今犹在耳侧,清晰得令人心动。
旁边的长剑苍黑慑人,一把暗鞘沉重非常,虽无丝毫花纹装饰,可一眼便知是剑中极品。
虽是极少见他身佩此剑,但这柄长剑毫不蒙尘,想来平日里亦是被他时常擦拭闲练的。
她小心翼翼地握住剑柄,将剑抽出来,只见剑身通体全黑,浑然无迹,有暗暗的犀光自剑刃两侧反射而出。
仔细一看,才发现这剑刃上纂刻着两行极小的字。
她微微蹙眉,拿起剑来慢慢看,待看清后,却是一愣。
“九天之上,我让你;九泉之下,我等你。”
这十四字是如此短如此简洁,可却是如此有力如此震人心神,叫她只觉背脊发紧,浑然忘却了本来在想什么。
殿门突然被人从外大推开来,她闻声回头,就见他步履刚健地走了进来。
“陛下。”她捧着长剑,看他阔步走近身前,弯唇冲他粲然一笑,搁下剑扑进他怀中,勾着他的脖子道:“陛下不在,臣放肆了。”
他一把将她抱起来放在长案上,双手撑在她身后案上,低头亲她的脸,“随你放肆。”
她错开脸,轻轻地笑起来。
他看见案上长剑,眉斜扬了下,立即收剑回鞘,道:“不会使剑的人,也不怕割伤了自己?”
她眨着一双晶亮的眼睛,“这剑真好看。”
他锐利的眉眼一下子变得有些柔和起来,薄唇轻扯,道:“此剑是当年父王赠与母皇的,后来又传给了我。”
她眉间一动,好像有些明白了长剑双刃上为何会被纂刻了字,不由喃喃道:“九天之上,九泉之下……”又抬眼瞥他,“这两句话真叫人心疼。”
他握着剑身的手紧了下,转而又松,“当年既灭中宛,父王自知伤重难愈,恐大行之后天下又起烽烟而陷将兵万民于战乱之中,遂出此策。”他眼底忽而涌起些温光,“可他算尽了诸事,却独没算到,他未死。”
当年的事情今朝又有几人能够说得清道得明,人皆以为他父王是为了所爱之人而让却这江山天下,却不知江山是什么,天下是什么,这生死爱恨又是什么。
他的父王一生骁悍,又岂是会为了女人而拱让家国天下的人?若非生死难料,若非心系万民,若非对方是他的母皇,恐怕父王纵是至死亦不可能会这么做。
她又探手去触了触那柄剑,神情变得有些恻然,轻轻点头道:“平王真男儿也。倘若换作是臣,臣必也会如此做。”她收手,看他又道:“疆土帝位之争,苦的从来都是万民百姓。既知自己会死,以一方帝业付与所爱之手,使这天下万民免遭战火荼毒,又有何错?”
他看她眼中潮润,不禁沉眉,伸手抚上她的脸,“可他终究未死,至今仍与母皇相守以共,享天下万民敬仰,威名亦将流芳百世。”
她咽泪而笑,抬手握住他的掌,“是,臣一时糊涂了。”说着,她放平了脸色,挪下长案,扬唇道:“臣好饿,臣是饿糊涂了。”
他知道她一夜半日都未曾进食,便让人摆膳入殿,牵着她的手一同落座。
她却凑近了他,双手伏在他膝头,瞧着他的俊脸道:“臣好像还从未与陛下一同用过膳。”
他淡淡地“嗯”了一声,一手用银勺舀了口汤送到她唇边,不紧不慢地抬眼望她。
她乖乖地喝下去,又抿抿了嘴唇,黑亮的眼睛笑得弯起来,“陛下对臣真好。”
他难得见到她将君臣体面抛在脑后的样子,看她如此乖巧,不禁低笑道:“今次怎的不灵牙利齿地进谏了?”
她静静地望着他,许久才细声道:“因为臣想任性一回。”
……因为,臣不知以后还有没有机会,能够如此任性。
他又喂她一口,眉目忽而一凝,“早朝时将你出使北境的事情发下外廷拟诏了,方恺欲让枢密都承旨汤成为副使与你同往,你意如何?”
她轻道:“好。”
他又低道:“此事既定,便不可久拖不行。中书计于今明两日修备所赍国书诸物,后日一早由殿前司亲兵护送你与汤成出京北赴潮安,至潮安后经由冲州至亭州,到时候狄念从军中派人至亭州接应,然后由禁军送你二人至金峡关。”
她想了想,却道:“至潮安后,可否改道由青州北上亭州?臣想顺路见一见沈大人与女学时的旧友。”
“也好,”他应道,“只是不可多做停留。到时再让沈知书抽些人马,与殿前司亲兵一同护你去亭州。”
她点头,淡淡一笑:“臣只见一见就走,绝不会久留。”
他的脸色也淡下去,“为何此番想见他们?”
她低了眼,半晌才道:“因为臣在潮安只有这一个旧友,自入朝以来便没机会相见过。”
……因为,臣不知以后还有没有机会,能够再见到她。
孟廷辉与汤成出京的阵仗毫不张扬。
天还未亮的时候,一千殿前司亲兵无声地护送着二辆马车从京城北门出城,直入通往北面诸路的官道。
皇上严旨,内外廷中不得有臣工为其饯行送别,十日后乃得告白天下,朝廷派文臣赴北境议和一事。
为防张扬,亲兵阵中没擎令旗,赴北一切事务皆由黄波统筹,奉皇上旨意,凡兵令皆出于孟廷辉一人。
她离行前并未知会过尹清。
不是没时间,也不是没机会,只是怕一不小心会另生事端,而朝廷派她出使北境的消息一旦传至北面,想来那边的人亦会有所准备。
汤成与她不算熟识,往日在枢府中也只是同僚之谊而已。她知道这是个本分人,所以才会被方恺择为副使陪她出使北戬,可越是如此,她便越不愿拖累旁人无辜者。
一路上并没什么不顺,直到行至潮安北路与成府路的交界处,才觉出这北面是真与从前不同了。
为防途中遇着流寇,黄波特意命亲兵绕道从西北面的成府路进入潮安一带,但此地虽离建康路甚远,却也能时不时地在官道两侧见到张惶的流民。
孟廷辉从京中出发前,虽知寇祸已自建康路漫向潮安及临淮二路的南面数州,可却没想到远在这成府路东面、与潮安北路交界的地方,竟也会看见因为寇祸战乱而流离失所的百姓们。
马车一路行,她的心就一路往下沉,可却更坚定了自己先前的决定是正确的。
待过了井桥县,正式进入潮安的地界后,天已是半黑了。
黄波疾速命人去前方官驿通报,然后亲自护送孟廷辉及汤成二人的车驾继续前行。
边路小县一带甚是荒芜,白日里下过雨,夜里的路就更加不好走。马车在泥泞道上颠簸慢行,依稀可见远方如稀星般的点点灯火。
孟廷辉在车中坐着小寐,忽听外面亲军士兵急急吁喝了一声马儿,紧接着又传来孩童尖锐刺耳的嚎啕大哭声。
她撩开帘子出去看,借着车头松脂燃光,就见不远处有个五、六岁的小女孩儿正被士兵从泥地里抱起来,不由微微蹙眉。
想来是因这道上太黑,亲军士兵行马未加注意,不小心伤了这孩子。可这里前后不见闲人身影,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一个人待在这种地方?
她让人将那小女孩儿抱到马车上,借光仔细察看了下,见其胳膊似是被马儿踢伤了,心中顿时一疼,吩咐人道:“带这孩子一起走,待入官驿后,叫驿兵去城里找个郎中来。”
黄波亦上前喝令其余人马行路时务必小心些,莫要再伤了人。
小女孩儿还在大哭,满脸泪水混着泥土,脏乱不堪,一口一声“娘”,声嘶力竭。
孟廷辉掏出帕子来给她擦脸,又将她抱进怀中,好声问她道:“你娘在何处?”
小女孩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两只小手紧紧拽着自己的衣摆,“娘……娘说去给阿乔找吃的,叫阿乔不要……不要乱跑,阿乔一个人待在地里好久好久,都不见娘回来……阿乔怕黑,阿乔好饿……”
孟廷辉连忙找出水食来给她吃,她却胆怯得不敢碰,口中只是要娘亲,两只乌黑的眼中溢满了泪水。
那边有士兵策马过来,禀道:“孟大人,这边流民不少,这孩子怕是被父母遗弃在这里了。”
孟廷辉点了点头,命车马继续前行,自己将帘子放下来,车中顿时变得一片晦暗。
小女孩儿在她怀中直打哆嗦,怕得要命。
孟廷辉摸了摸她的头,轻声道:“莫怕,我不是坏人,待一会儿等车停了,便找郎中给你看胳膊,立马就不痛了。”
她咬着手指掉眼泪,噙着泪的大眼睛望着车帘,细声道:“他……他们会杀人……杀好多好多人,阿乔的爹爹就是被他们杀的……”
孟廷辉心头一梗,知道这孩子尚小,分辨不出什么,看见持抢骑马的士兵便以为是作乱的贼寇,当下紧紧抱住她,轻轻道:“放心,不会再有杀人的坏人了。”
小女孩儿张着大眼瞅她,脸上都是畏惧之色。
孟廷辉拿过水来喂给她喝,慢慢地同她说:“你可知,我大平的皇上是个好皇上,一听说这边有坏人作乱,就立刻让我来警告那些坏人,不可欺我百姓,否则他们亦没好下场。那些坏人一听是皇上这么说了,立刻就不敢再胡乱杀人了。”
小女孩儿仍旧瞅着她,小声道:“真的?”
她点头,语气极其笃定,“真的。”她想了想,又道:“只要皇上在位一日,就绝不容百姓们受这种苦。”
小女孩儿一下子埋头钻进她怀中,又小声嘤嘤地哭起来,“娘……娘是不是不要阿乔了……阿乔不吵着要吃的了,娘回来好不好……”
孟廷辉官服前襟一片暖湿,浸得她心口都潮润不已。她低头轻望这小小女孩儿,就如同看见了当年的自己,幼小无依,孤苦无靠,倘是没有遇着她,是不是就会死在这荒郊野外?
夜风起,吹得马儿嘶鸣荒草凄沙。
此地尚且如此,更遑论那些被寇军侵占掠袭的州县了。
若是她身可济民,她亦不所惜也。
……
在井桥镇官驿的这一晚,她做了整整一夜的噩梦。
梦中有血有厮杀,有宫殿有破庙,有人饮笑有人流泪,有人哭喊有人吵闹,事事狰狞。
第二天一早醒来时,身下床褥都被冷汗浸透了。
天蒙蒙亮时,黄波便来请她上车,深怕这潮安西界处会遭贼寇来扰,恐她人有安危,只催她与汤成早些赶往青州。
孟廷辉自己也明白此地不可久留,但又嘱咐人将那小女孩儿好生安顿了,倘是可能的话替她寻寻母亲,官驿里的人不敢不应,忙不迭地安排去了。
清晨之风颇为凉爽,朝阳初露,马儿飒行,一众兵马蹄踏愈急地往青州赶去。
途中暂歇时,连平常不善多言的汤成亦黑着脸色,同她连连叹了好几口气,显然是也没料到北地会变成眼下这个样子。
过井桥镇往北数十里后,路就渐渐好走起来,快马加鞭地赶了一日余,终在天黑之前到了青州城外。
沈知书闻报,亲自出城十里来迎。
骏马扬蹄,人影清瘦,转运使的令旗逆着夜色高擎在后,如同在黑暗中乍然扫过的一抹亮光,令她远远一眼望见,心头阴霾顿时褪去不少。
一入青州城,黄波这才稍稍放下心来,在马上正身向沈知书揖了礼:“沈大人。”
孟廷辉早已使人将车停下,下来换马而行,又冲催马在前的沈知书道:“我在青州只得一夜的空儿,你且直接带我去严家罢。”
沈知书在马上的背影微微一僵,没回头亦没吭声,只是利落地一勒马缰,拨辔转向另一边行去。
而在他转身侧脸的一刹,她才瞧见他那张俊脸不知何时添了道细疤。
| 上一章:章六十 兴亡 | 下一章:章六十二 意决 |
2020 © 所有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
www.shenlanqiyu.org Powered by 神澜奇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