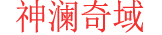
续:燕红卷 梨花 · 下
| 上一章:续:燕红卷 梨花 · 上 | 下一章:续:保卫西蒙 逆鳞 |
天才一秒记住本网址,www.shenlanqiyu.org ,为防止/百/度/转/码/无法阅读,请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本网址访问本站,记住了吗?
远远地,燕洵点了点头,说道:“你先好好歇着,朕晚上再来看你。”
大门敞开,有清新的风吹进来。
纳兰坐在榻上,默默的望着他远去的背影,面容温和,目光如天上的浮云,那般宁静。
“娘娘——”
文媛开心的笑,几乎不知道该说什么,终于一头冲了出去,嚷嚷道:“奴婢去准备一下。”
纳兰深吸一口气,靠进软绵绵的被子里。突然记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黄昏,他骑着马,远远的追上来,最终站在桥头上对着远行的她,大声的喊:“我在梨花树下埋了好酒,你明年还来吗?”
你明年还来吗?你明年还来吗?还来吗?
多少年了,只要她一闭上眼,就能听到这个声音。似乎就在昨日,就在耳边。
“来!你等着我!”
她坐在马车上,探出头,冲着已经变成一个小黑点的他大声的喊。
来!你等着我!
然而,她终究没能再回去。
她父皇驾崩,独留下她和病母痴弟,和满朝狼子野心的皇亲权臣苦苦周旋,江山家国通通落在了她单薄稚嫩的双肩上。
而他,却家破人亡,流离失所,昔日的天之骄子,转瞬成了阶下之囚。
十年生死两茫茫,他们终于再一次回到了昔日相遇之地,只可惜,山河已碎,物似人非,纵然相对,却已不再相识。
她缓缓的闭上眼睛,嘴角轻扯,带出一个浅浅的笑容。
天还没黑,文媛就忙碌起来,为她搭配衣衫,为她梳妆打扮,厨房里的下人知道皇上还来吃饭,也卯足了劲准备了起来。她虽然不愿这样,可是难得见她们这样高兴,也就没有反对。
然而天色越来越暗,早已过了晚膳的时辰,还是没见他来。
所有的下人都在暗暗着急,文媛派得力的下人出去打听消息,自己则一遍一遍的安慰着纳兰。
纳兰心下却渐渐了然,然而也不觉得如何伤心,只是觉得有些空旷。玉树说的对,东南殿太大了,总是显得冷清。
不一会,燕洵身边的小太监跑来传话,说是西北美林关传来紧急军情,皇上今晚在军议处和几位大人议政,就不过来了。
那一刻,纳兰几乎能清楚的听见整个大殿传出来的叹息声,她面色从容的和那名传话太监对答,打了赏。对文媛说:“好了,摆膳吧。”
文媛一愣:“啊?”
纳兰失笑道:“用膳啊,皇上不来了,难道本宫就不用吃饭了?”
文媛这才醒悟,连忙带着失魂落魄的下人们传膳。
纳兰自己一个人,吃了二十多道菜,她今天的胃口似乎格外好,精神也好,吃了很久,才叫下人上了汤。
随后三天,燕洵一直忙于军事,靖安王妃赵淳儿当年战败之后退入南疆,纵然遭到诸葛玥的几番围剿,仍旧侥幸逃了去,而诸葛玥碍着赵彻的情面,见她不再攻打卞唐,也没有赶尽杀绝。可是近期,西北却有消息传来,说靖安王妃的人马和关外犬戎人走动频繁,恐怕有变。
一时间,各种情报火速传往京城,大燕朝廷顿时紧张了起来。
这三天,纳兰的病情几次反复,东南殿愁云惨淡,一片冷寂。
这天晚上,已经三日不曾下榻的纳兰突然坐起身来,要文媛将她那只放在柜子里的锦盒拿来。
文媛本来想劝她不要操劳心神,可是见她神色坚定,也不敢再说什么。
一只香檀色的锦盒,看起来已经很旧了,并不沉,拿在手里,轻飘飘的,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贵重的东西,竟然并排上了三把锁。
文媛用帕子弹去盒子表面的灰尘,不由得咳嗽了起来,只见那灰已经积得很厚了,也不知道放了多久。
纳兰接过盒子,默默的看了一会,然后从枕头下面拿起三只钥匙,将盒子打开。
文媛伸长了脖子,只见盒子里装着的竟是厚厚的一摞书信,有很多信纸已经泛黄,看起来年代十分久远。她不由得有些失望,纳闷的皱起眉来。
“文媛,去拿一只火盆进来。”
“娘娘,你要火盆做什么啊?”
纳兰指着那些书信,说道:“烧了这些。”
“啊?烧了?”文媛一愣,虽然她不知道这些信是什么人写的,但是只看皇后放的地方,就知道定是十分重要,忙问道:“为什么呀娘娘?为什么要烧掉?”
纳兰若有所思,轻轻道:“不烧掉,还留给别人伤心愧疚吗?”
文媛显然没有听懂,可是却乖乖听话的走了出去,不一会,就拿进来一只火盆,炭火劈啪作响,暖意融融。
“文媛,你先出去吧。”
文媛点了点头:“是,娘娘有事就叫奴婢。”
殿门被关上,大殿里又安静了下来。纳兰拿起那厚厚的一摞书信,苍白的手指摩挲着那些不知道已被她看过了多少遍的信纸,目光渐渐柔和了起来。
是的,姑姑说的对,她是个胆小鬼。
什么长公主的尊严,什么怀宋的国体,什么纳兰的姓氏,全都是假的,全都是自欺欺人的。她只是害怕,只是没有胆量,只是不敢跨出那一步。
他不知道一切,那么当她看到他怀念玄墨,看到他对玉树、对永儿多加照料,她就会觉得甜蜜,就会觉得他还是重视自己这个义弟的,就会知道自己在他心中还有有地位的。
可是一旦他知道一切之后,却并未爱上她,那叫她情何以堪?
她害怕,她没有勇气,她害怕一切挑明之后他也只是微微震惊,却无法回应她所期盼的感情。她害怕自己孤注一掷之后,却还是无法同他心底的那个人一较长短。她害怕真相摆在面前之后,她还注定是失败的那一个,却连继续幻想继续做梦的权利都没有,最起码现在,她还可以骗自己说,自己和那个人,是一样重要的。
看吧,她就是这样懦弱的一个人,明知道是自欺欺人,却还要顽固的坚持着。
可是,又能怎么办呢?她的爱情,就是一棵不结果子的树,她害怕秋天来临的那一刻,所以就固执的留在春夏,这样,就不用去面对那惨淡的结局了。
她拿起一张泛黄的信纸,墨迹淋淋,她的手高高举起,指尖苍白纤细。信纸放的久了,已经又薄又脆,发出清脆的声音,突然,纳兰轻轻的松开了手,信纸滑落,火盆里的火舌顿时扬起,一下将那张她珍视了很多很多年的书信吞没,转瞬之间,就化作飞灰。
当年派玄墨去东南,她并不是想害死他,也并不是想要夺他的兵权。
当时怀宋积弱,各方军队蠢蠢欲动,她有意借燕北之力挽救纳兰氏挽救怀宋百姓于万一,可是朝野上那些对江山有意和愚忠的朝臣却不肯答应。那个时候,谁将国家献出去,谁就是叛国的逆臣,谁就会遗臭万年,永世不得翻身。她只是不想让数代忠贞的玄王府替她背上这个骂名,才将他远远的调离中央。并且害怕他手下的亲兵会有所鼓噪,若是部下群起进言,就算玄墨不肯答应,将来燕洵主政,燕北的大臣也会为玄墨罗织罪名,所以她才调走他的部下,让他去统领和他完全不相干的东南海军衙门。
然而,她千算万算,没料到东南贼寇会趁怀宋内乱而联合起来攻打东南衙门,也没想到玄墨以堂堂亲王之尊,会亲自披甲上阵,冲锋杀敌。
想来,她会有今日,也是报应。
她从政多年,手上染血无数,一道圣旨,便是千万颗人头落地。从来落子无悔,她明白,她全都明白。
所以,当她看出来他每月都在算着日子来她的宫殿之后,她就突然明白了,他不想要她为他生下孩子。
纵然她曾经为了稳定朝野,答应过怀宋群臣,定会保住宋臣的地位,定会让下一代燕皇身上流着怀宋的骨血。但是在这件事上,她却不愿再去勉强,也不愿将他们的一切,都烙上政治的标签。
这,是她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任性。
以后的每次临幸之后,她都会吞下苦药,将一切他所担忧的扼杀掉。直到后来,他来的次数越来越少,而如今,他已是两年未在东南殿过夜了。
她这一生,所求的都如指尖流沙,越是想要握紧,越是逝于掌心,如今,已经什么也不剩了。
火舌蔓延,一封封书信被烈焰吞没,大火烧掉了他们相识的最后凭证,一点一点,连同她这支离破碎的人生,一同付之一炬。
有的爱是甜蜜,有的爱却是背负,她自己辜负了玄墨,一生愧疚,如今,她就要死了,又何必让他知道一切,然后一生愧疚与她?
他这一生,已经足够苦了,她又何必在累累伤口上,再洒上一把盐?
烧吧,都烧掉吧。
世人都道富贵荣华,都道权倾于世,可是却唯有她知道,唯有她看到,那满目锦绣之下,隐藏的是怎样一颗累累伤痕的心。
不是不够爱,只是爱不起。
她和他都一样,背负着太多责任,背负着太多使命,任性不起,冲动不起,热血不起,更天真不起。
烧吧,都烧掉吧……
浓烟升起,她开始低沉的咳嗽,有腥热的液体缓缓流下。依稀间,似乎还是那年春花如繁,白梨粉杏飞扬如初晨云霞,他衣襟飘飘,立于三月春园之中,暮然回首,眼眸若星,嘴角含笑,打趣的望着冒然闯入的她,眉眼细长,目光炯炯,轻笑着问:“迷路了吧?哪个宫里的?”
她一身男装打扮,脸蛋涨的通红,鼓足了勇气开口,声音却仍是极小的:
“我、我是怀宋安陵王之子,我叫玄墨……”
也许,一开始就是错的。
韶华春遇,明艳晨光,终究还是被这场颠沛流离的乱世烟尘覆上了沉重的埃埃土灰。天空明净,却也早已不是当日的云朵彩霞,看不见的刀光剑影一重重割去了当初的曾经的年少天真,留下的,不过是残垣断壁,在暗夜中闪烁着暗黄的斑影,可笑的对那些逝去的简单岁月,固执的念念不忘。
他的一生,唯有两个人是最重要的,一个,已经被他亲手放逐而去,另一个,却终将成为他最挚爱的兄弟,永远的活在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
只可惜,这两个人,一个也不是她。
大殿里灯火辉煌,可是在她看来,却好似隔了一层暗红色的纱,蒙昧阴郁,暗淡无光。
这一生,坚忍执着,几番风雨,终究化作一场无声的酸痛,落在冷寂的深宫之中。万千生灵、血雨腥风尽皆静静的被一双素手翻转,如今回眸,只觉惫倦沉浮,刹那芳华,浮生若梦,恍然落入茫茫归墟。
掌中信笺蓦然间若雪花滑落,轻轻飘荡,散落一地,火盆中黑灰倒卷,呼呼作响,幽幽上窜,吞吐着苍白的火舌。
她惘然一笑,手腕无声垂下。
燕太祖开元五年,十二月初四,夜,大雪,皇后纳兰氏,薨于燕离宫东南殿。
“皇上。”
内侍在身后低声说道:“找到了。”
燕洵缓缓回过身来,东南殿如今已经空寂下来,大殿里空无一人,皇后丧期已过,东南殿的旧人都已分配各宫,如今留在这里的,只有两名年迈的内侍,负责一早一晚的洒扫。
打开盒盖,是一件乌金色长袍,上绣青云纹图案,两襟有着小团福字,看起来简约华贵,只是左边的袖口处有一道口子,已经被缝合,若是不仔细看,几乎看不出来。
燕洵站在那里,默默的看了许久,终于抬起头来,将衣服交给下人,说道:“回宫。”
“是。”
一众下人跟在他的身后,大殿的门大敞开,寒冷的风吹进来,扬起满地细小的灰尘,殿外的阳光有些刺眼,他微微眯起双眼,站在门前,突然回过头去,看向深深帷幔后的那方软榻,似乎还是一月前,她坐在那里,轻声的问:“今天晚上,臣妾吩咐厨房多做几样好菜,皇上你,还来吗?”
皇上你,还来吗?
阳光刺入眼底,让他的心突然变得荒凉。
仅仅是一时的耽搁,不想,却成了永别。
他的眉轻轻的皱起,又缓缓松开,一点一点的,消泯了那丝悲凉之气。
抬脚就要走,突然嗅到远处有一丝烟尘之气,他转头看去,却是极远处的一个拐角,一名小宫女蹲在那,正在烧着什么。
他微微一愣,带人就走过去。
那名宫女见了他,顿时一惊,整个人跳起来,连忙跪在地上请安。
燕洵看着她,微微皱起眉,说道:“你是以前皇后宫里的文媛?”
“是,奴婢是。”
“为何在这?”
“这是皇后娘娘的旧物,娘娘去前说过要将这些杂物都烧掉,这些日子奴婢被调到了安嫔娘娘处,一直没有时间回来,今天得了空,就回来料理一下。”
燕洵见文媛穿着一身低等奴婢的衣衫,脖颈上还有淡淡的红痕,知道皇后去了之后,她宫里的旧人定是在别处受了欺负。默想了片刻,问道:“你家在何处?”
文媛一愣,没想到皇上会问起这个,连忙答道:“奴婢是跟随皇后娘娘来的,奴婢的家在宋地。”
“家中可还有人?”
“回皇上的话,家中还有老父老母,三个兄长,两个姐姐,一个妹妹。”
燕洵点了点头,对一旁的下人交代道:“传令司奴局,赐她四品兆荣女官之位,享正五品朝官俸禄,另赐黄金百两,即日就出宫,送她回乡吧。”
“是,奴才记住了。”
文媛似乎是听傻了,就那么跪在那里,久久也不说话。反而是那名内侍笑着说道:“兆荣女官,高兴地傻了,还不领旨谢恩?”
文媛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,一个头就磕在地上,大声叫道:“多谢皇上天恩,多谢皇上天恩。”
燕洵也不做声,目光在那满地白纸上淡淡扫过,终于就这么的,转身而去。
雪已经停了,天空那么蓝,蓝的如一汪碧水,风从远处吹来,卷起一张信笺,就那么轻飘飘的飞起,穿过火舌,信尾曲卷,微微烧了起来。那封信就那么飘荡在风中,向着那人远去的方向追去。
很多年前,在一盏孤灯之下,垂死的将军用尽最后的心力,勉力提笔,写了这封信。这封信经过了很多人的手,然而却没有任何人觉得不妥。那不过是写给燕北大皇的一封普通信件,上面详述了怀宋在大夏边境的屯兵兵力,后方常驻军队,各位边境将军的脾气秉性和优点缺点。
然而,当今世上,能看懂这封信的只有三个人,而其中的两个,都已经不在了。
刚劲有力,笔走龙蛇,上书玄墨的大名和印玺,可是字迹,却绝不是那个与燕洵写了很多年信的故人。
风继续吹,那封信追在燕洵的身后,盘旋着,飞舞着,火舌一点点的从后面蔓延上来,烧过了信头,烧过了问好,烧过了请安,烧过了一半……
风突然猛了起来,那封信呼的一下高高的飞起来,眼看着就要越过前面那人的身影。然而这时,一棵梨树突兀的出现在眼前,信纸高高的挂在梨树之上,只差一个身位,就能赶到那人的前面。
燕洵却微微一愣,他静静的看着那棵树。想起来小时候,他就是在这里,第一次见到玄墨,那时的他迷了路,傻乎乎的到处乱走,一张小脸急的通红,像个害羞的小姑娘。
“皇上?”
内侍轻轻的叫:“皇上?”
燕洵回过神,嗯了一声,转头就向着宫门而去。
火舌一点点蔓延而上,在那株梨树的阻拦下,将那封延迟了五年都没能送出去的书信,一点点的吞没。终于,只剩下一段软软的黑灰,挂在树梢之上,风过处,扑朔朔的零落成万千飞灰。
极远处,仍旧在哭泣的小宫女拾起地上的其他信件,全都倒进火盆里,大火呼啦一声烧的老高,扬起鲜红的火焰。
纵然情深,奈何缘浅。
曾经是这样,从来,都是这样。
史料:
开元六年,纳兰皇后寝陵竣工,坐落于燕北落日以南。
二十三年后,燕太祖驾崩,葬入太极陵,太极陵位于落日山以北,与纳兰皇后陵寝遥遥相望。
赤水支流铅华江流经此地,贯通两陵,因寒冬飘雪,落于江面之上,类似梨花,当地人又称此江为“梨花江”。
【燕红卷完】
| 上一章:续:燕红卷 梨花 · 上 | 下一章:续:保卫西蒙 逆鳞 |
2020 © 所有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
www.shenlanqiyu.org Powered by 神澜奇域